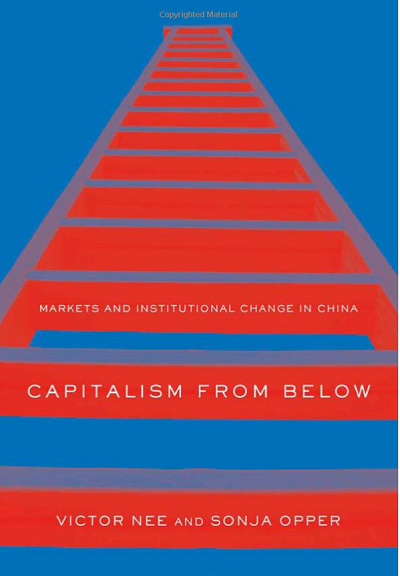新上任的社会学系主任临时更改博士生中期考核要求,将上学期已经完成的考试作废。新试题有一项是让我们枚举当代中国转型研究的新概念和新理论。
我现在正为博士论文写作手忙脚乱,就随便找了五本著作,应付一下。。。
当代中国研究从来不是国际社会学的主流,中国转型更不是国际社会学关切的议题。以美国社会学会会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为例,2004-2018年已刊发的论文中仅有10篇涉及中国问题,这10篇论文中甚至还包含两篇comment article而非research article。以应邀综述称著的Annual Review出版社也并未对中国问题有兴趣,1990-2018年刊发的669篇论文中只有4篇以中国为主题。美国社会学三大刊的另外两本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Social Force近10年涉及中国研究的论文分别为14篇和15篇。这个出版情况说明,只有极少量的中国研究论文得以在国际社会学的顶级期刊发表。以此类推,包括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在内的绝大多数当代中国研究对人类学术知识的积累尚谈不上有深刻的影响。(老觉得全世界重要社会科学家都在研究中国的人,要么对国际学术发表有什么误解,要么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几篇文献。。。)

但就社会转型这个议题本身而言,中国转型研究并非独树一帜。从ASA提供的注册会员信息来看,从事社会转型研究的学者为数可观,大部分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生命历程。以任教于北美和欧洲高校的社会学者为例,他们包括研究坦桑尼亚社会转型的Ron R Aminzade,研究巴西社会转型的Anthony Pereira、Luisa Schwartzman,研究韩国社会转型的Jaeeun Kim、Gi-Wook Shin,研究拉美社会转型的Larry J. Diamond、Miguel Centellas,研究波兰社会转型的Geneviève Zubrzycki,研究捷克社会转型的Paul Froese,研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Deborah Kaple,研究匈牙利社会转型的Iván Szelényi等。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学界关注中国转型的中青年则是Eli Friedman、Bin Xu、Ethan Michelson、John Aloysius Zinda等。
以下简要介绍我随手检索到的五本著作:
1.State-Led Privatization(国家牵引的私有化)
Julie Zeng(2013)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私有化经济的出现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她认为过去研究把近30年中国私有化经济腾飞视为一种自发的行为是不合理的解释。私有化经济成份在全行业的涌现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有明确时间表和可度量私有化比重的国家性行为。这个过程之所以由国家引导,目的在于把市场限制在党的可控范围之内。通过在沈阳、上海和厦门三城市对民营企业进行田野调查,Zeng细致考察了中央领导层、基础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多层级互动关系,这一关系形塑了中国私有化的基本轮廓。一方面,当地的经济结构和干部考核体系提升了地方官员实施私有化的积极性,于是在应对私有化反对势力上,地方官员能坚决针对各种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和反征地运动采取强而有力的压制手段;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同时也提升对各种舆论的反应能力,能在政治控制环境出现变化后对地方官员进行调整。总而言之,中国的私有化经济出现及其发展是国家引导下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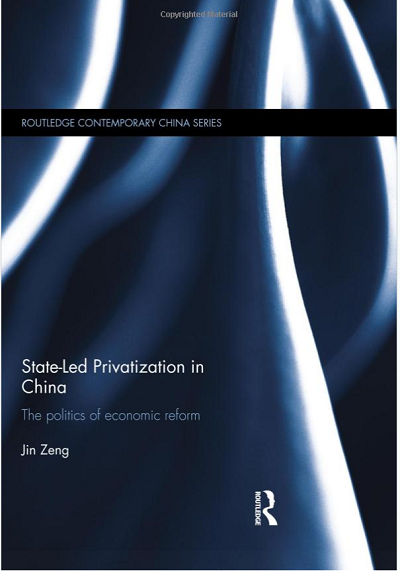
2.growing out of the plan(计划外增长)& gradualism(渐进主义)
Barry Naughton(2006)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两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一个是growing out of the plan,另一个是gradualism。Naughton认为自中国宣布实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以来,其经济表现之优异超过了几乎所有学者的想象。中国不仅成功保持超过三十年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还较为顺利地避开了2008-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举迈进世界上最庞大经济体行列。中国这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既相似又有所区别。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始于中央政府的经济改革规划并得益于一系列地方政府的保增长经济政策。而且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其他基础条件全方位落后的情况下启动的,由此来看其增速和增幅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经济体。
Naughton认为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考虑改革者关于转型过程的设想和目标,是他们设计出一种有特色的市场转型方式并最终形成渐进式的转型战略的。首先中国在早期阶段实行的是行政审批权逐级下方和价格双轨制这种渐进改革手段,在经济基本目标达成之后就决然废除几乎全部的指令性经济功能并在所有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意外的是,中国在没有放弃国家垄断原始生产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资源和能源)的情况下,还能发育出多种所有制并存竞争的新经济形态。这种“上游完全垄断和下游完全竞争”的局面是改革者所没有预设到的,同时他们也不打算在未来减少或消除这种扭曲的经济现象。相反,他们还会在牢牢把控上游资源的前提下,继续有计划地开放下游竞争市场,鼓励资源流到那些可以扩大就业和创造价值的领域。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都能预期在中国庞大的“利基(niches)”下获益,后者如同海绵一样不断吸纳更多的资本,从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一经济成绩是在最小经济动荡和相对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完成的,与之相较,东欧诸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呈现长期经济下滑和时不时的社会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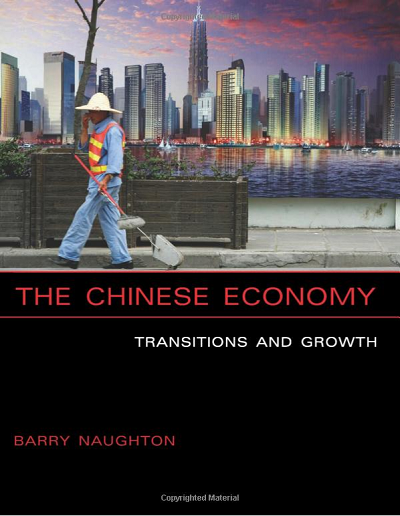
3.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社会火山口的谜团)
Martin King Whyte(2010)通过一项全国性调查研究中国人对社会不平等的看法,他发现种中国人现行社会制度基本满意,没有任何“社会火山”等待爆发。这副图景与中国严峻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恰好相反。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自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已从世界最平等的社会之一(1980年的基尼系数为0.29)变为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2005年基尼系数超过0.45)。与此同时,中国经历了显着的经济增长,甚至在社会底层也获得了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根据Whyte的调查,绝大多数中国人(71.7%)认为不平等水平过高,认为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似乎存在一座一触即发的“社会火山”。但被调查的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也认为穷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他们不赞成政府将财富从富人截取并重新分配给穷人。他们倾向于像自由福利国家那样建立起健全的社会安全网,通过积极的扶贫行动计划来帮助穷人向上流动。尽管中国人并不认为当前社会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他们普遍接受目前的不平等,并且在这方面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民更乐观。总的来说,中国人认为财富更多应来自自身的努力而不是经济欺诈或福利偏袒。Whyte使用多种复杂的统计技术来分析这些态度如何因地理位置和社会阶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其中城市工人比农村农民更加喜欢批判不平等,尽管农民普遍徘徊在贫穷线附近。另一方面,农村劳务移工比任何其他职业群体都更为关注不平等,低技能工人对不平等的不满也比高技能工人来得多。当Whyte的团队询问受访者有关政府按市场绩效进行收入调整的意见时,他们答案非常复杂,最穷的受访者反倒不喜欢完全平等,其次才是最富有的人。
Whyte的研究结论是令人惊人的。中国人更能忍受市场驱动的不平等,并且不在意当中有政治力量的掺杂。Whyte的调查表明中国人早已普遍感知到收入不平等的严峻性,但不同群体的人在不平等的缘起和影响上毫无共识可言。因而人们对不平等的抱怨无法产生动员广泛的社会运动,也没有可能对现行制度构成政治挑战。甚至大约50%的中国人认为政府并不关心他们的意见,他们仍然对当前的制度相当满意。这说明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背后是有着极其复杂的机制。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保持了8%-10%的惊人速度,这种增长的副作用就是社会不平等。可是人们更关心的是巨大经济增长为社会各个层面带来了新的机遇。大多数中国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普遍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并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富裕群体的一员。Whyte的著作从另一角度说明社会不平等的后果并未如西方社会学者早前所设想的那样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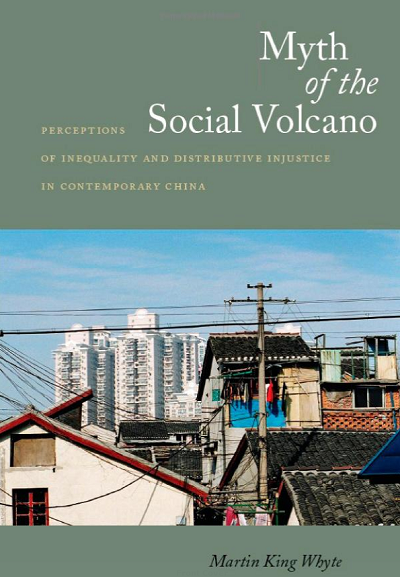
4.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无民主的资本主义)
Kellee S. Tsai(2015)研究过去30多年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当前中国私营企业超过3000万家,雇佣超过2亿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尽管国际政治观察家和全球商业领袖乐观地预测市场资本主义会给中国带来政治民主改革,这一愿景却迟迟没有实现。在缺乏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政府的全部精力集中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国本土企业家不会也不鼓励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追求西方民主。这是中国高度经济繁荣背后的基本政治图景。
Tsai的研究揭示,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大多数劳动者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维持企业的高速运转。许多中国企业家十分认可这种劳务安排并认为这是中国企业相比跨国公司的最大竞争优势。Tsai发现中国企业家的日常活动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比传统政治理论中的街头游行、投票、游说和抗议更有影响力也更有效。事实上,正是那些创造了庞大就业机会的中国企业家,他们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的劝谏,使中国经济部门进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与中国政府官员的谨慎合作中,中国企业家创造了一套非正式的适应制度,它反过来又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监管环境。Tsai研究的这项研究持续了十多年时间,实打实地与私人企业家进行了数百次面对面访谈。中国这种无民主的资本主义现象打破了我们过去对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之间关系的刻板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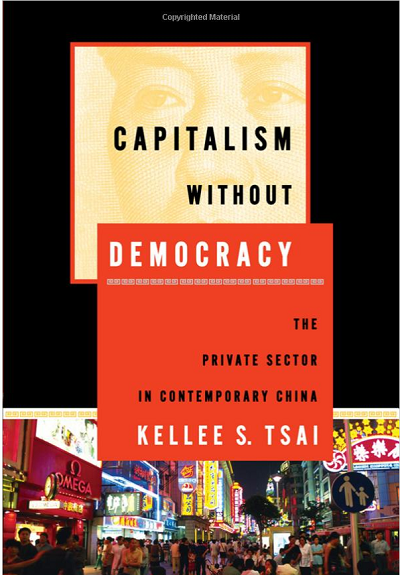
5.Capitalism from Below(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关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哪个在中国先出现?Victor Nee(2012)在他关于中国市场和制度转型的新著作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指出,中国经济不是政府部门从顶层制度设计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底层民间经济组织中生长起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允许企业家在不完善的制度底下建立市场供应链、培育消费者和对外融资。按Nee的说法,“中国私营企业经济的出现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既不是其政治精英所设想的,也不是他们预期的”。
Nee详细考察了中国早期企业家与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脱钩的过程。起初中国政府没有为私营企业提供土地产权,也中国内部也不存在财力雄厚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帮助。企业家靠自己反复试验突破重重困难,在十分不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底下发展出自己的经营模式。这些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促就了中国制造业的惊人发展。直到这些企业获得成功和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谋划正式的经济规则。
Nee为了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路径,对中国法律部门以外非正式经济规范进行了详细回顾。由于私营企业家的利益与政府部门僵化的激励结构不一致,他们没有因循守旧地遵照政治惯例,而是通过大胆的制度创新谋求自身的发展。Nee认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在最初阶段执行强而有力的管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默许这些企业改变正式规则,以便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策略保持一致。基于长三角地区700多家企业的历史资料,Nee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缔结非正式契约的过程。得到这些关系的保证,企业家摸索中学会了如何在市场经济领域开展业务。他们能敏锐发现市场机会,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借助民间力量克服融资问题,进而演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虽然随着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政府不断完善《劳动法》等正式制度,确立了完备的劳动雇佣条件,但这些企业依旧保持着创新的活力和竞争优势。中国私营企业的创新不是从天而降的。为了同国有企业竞争,这些私营企业必须竭尽全力进行技术改良和突破。技术累积不仅对企业自身非常重要,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自下而上发展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氛围下,许多企业得以开发新技术、设计新经营模式和规划新产业。
中国当代经济转型与企业发展是一项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课题。Nee以私营企业发展史为开端,进一步探讨政治资本对私营经济成功的重要性。过去研究指出,裙带资本主义在中国非常猖獗,政治性寻租在全行业非常普遍,然而Nee没有这样考虑。他发现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干部身份、党内业绩以及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都与其盈利能力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关系。Nee判断,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的成功绝不是因为裙带资本主义,而是企业自身的市场价值。Nee指出,“市场出现的结果是政治资本价值回落。随着市场的壮大,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小,阻碍或打击市场经济的政治因素被降到最低”。
Nee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发现了自由企业的制度可以在没有政治规则的情况下获得发展。Nee揭示了私营企业背后的整个供应链、劳动力投入、产品研发和创新以及企业启动资金都可以自下而上发展起来。所有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互动都是企业家自己的行为,政府部门所做的只是顺势而为引导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