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转自美国ABC广播电台。中国资本进入赞比亚,为大量的赞比亚本地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全球中国的幽灵》。
作者:Ching Kwan Lee
翻译:Ging Lam
“双重自由化后(dual liberalization)”的赞比亚
赞比亚地处非洲中部铜矿带的南部边缘。该国人口有 1300 万,主要集中在首都卢萨卡(Lusaka)和一些铜矿区的城镇。尽管赞比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人均 GDP 只有 1540 美元,且自给自足的小农产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是最大的单一雇佣部门。从最早有人定居的历史算起,赞比亚就是不同班图语族群聚居的家园。19 世纪 80 年代,罗德斯的英国南非公司(Rhodes’s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征服了这个地区——并非没有战争——然后割让给伦敦政府。长期以来,伦敦政府一直统治着这个北罗德西亚地区(Northern Rhodesia)。到20 世纪 20 年代,当地丰富的铜矿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和南非的矿业金融家;甚至在1945 年,赞比亚的铜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 13%。当由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于1964 年领导赞比亚取得国家独立时,赞比亚被认为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具有实现全面工业化的良好前景。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于1972年所撰写的鼎鼎有名的专著《铜矿的阶级成色(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为我们了解赞比亚矿业在这一时期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基准参考,有助于我们确认非洲背景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目前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分析中常常被抹杀。相隔四十年,我们在同一个矿区进行实地考察。不同的是,在这期间,世界经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洛维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传记中写道,他正在研究从殖民统治中进行转型的阶级利益重整现象:尽管这一“赞比亚化”过程让赞比亚政府获得了51%的矿产资源股份,但还有两家西方公司保持着对赞比亚矿产的寡占控制。布洛维发现,在对外经济依赖的背景下,赞比亚的政治独立造就了一个有缺陷的黑人统治阶级(flawed black ruling class)——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外国资本的挑战,而是与外国资本的利益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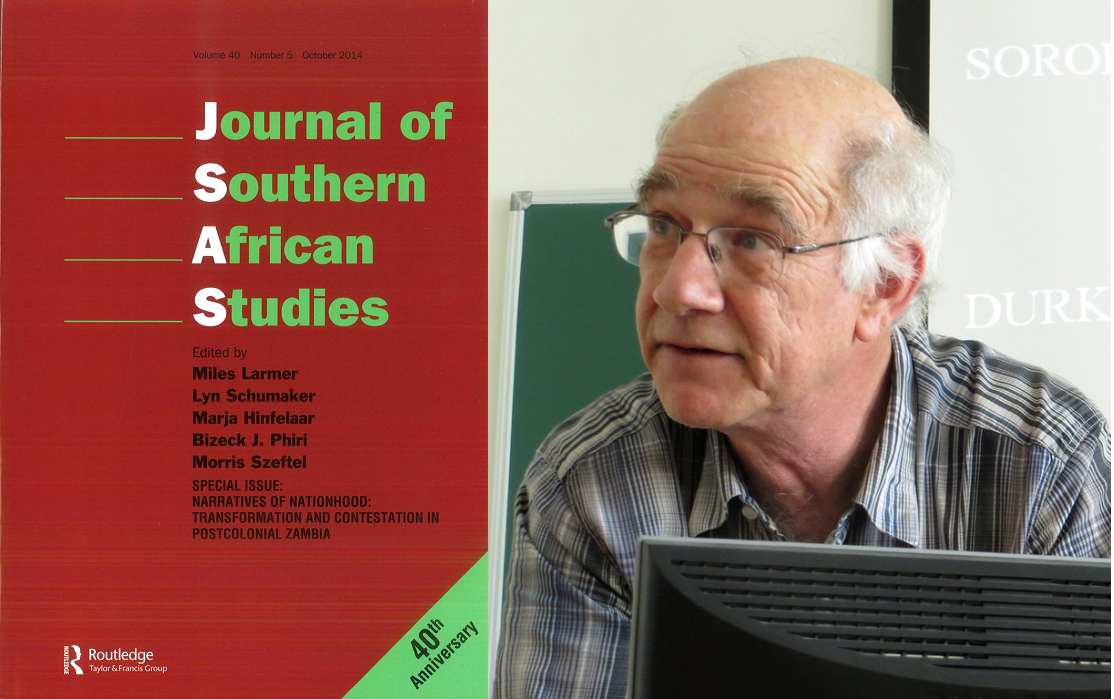
1972年,迈克尔·布洛维在其成名作《铜矿的阶级成色》中使用了英国人类学鼻祖之一、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领军学者雅普·范·韦尔森(Jaapvan Velsen)所亲自教授的扩展案例分析法(extended case method)。基于该方法,布洛维学会了情景分析(situation analysis),即在广阔的经济、地理和历史背景下确定社会进程的位置。但韦尔森对布洛维应用该方法于赞比亚的研究公开表示不以为然——曼彻斯特学派强调经验的中心性,案例的延伸存粹通过经验手段,尤其是对经验的直觉类比;但布洛维却坚持理论的中心性。42年后,也就是2014年,布洛维为《南非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特刊《国家叙事:后殖民赞比亚的转型与争论》撰写长文《对阶级成色的修订:赞比亚后殖民主义四十年》,对早年的研究进行重新修订。该文指出先前研究存在许多缺陷,而理论的局限性是其主要缺陷之一。但这并非是对曼彻斯特学派的妥协,而是早前研究对“赞比亚化(Zambianisation)”这一核心概念的描述及其所依赖的语境的延伸,都是以经验主义的发现形式呈现的,没有自觉发展成所依赖的理论。
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球铜价大幅下跌,赞比亚立即陷入债台高筑境地,并且高度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由于卡翁达政府(Kaunda government)这时完全拥有并管理着铜矿,这一时期亦是赞比亚紧急启动一党专政的时刻。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83至1987年对赞比亚实施了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包括在通胀居高不下情况下冻结了工资发放,同时大幅削减食品补贴、化肥补贴及政府支出。早了1991年,因为建筑工人工会领导、弗雷德里克·齐卢巴(Frederick Chiluba)任主席的多党民主运动联盟(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即MMD)在选举中获胜,民众和工会对国家紧缩政策的抵制达到了顶峰。齐卢巴上任后立刻改变了立场,推行了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激进私有化计划——包括采矿、土地、交通、能源等——并取消了劳工权利。在上世纪 60 年代时,来自铜矿的税收收入曾一度占赞比亚政府总收入的 59%;但到本世纪初,由于政府在铜矿私有化后与外国公司签署了对投资者极为友好的开发协议,这一比例立马大幅下降到仅有5%。在“双重自由化”背景下,即在经济转向私有化和拥抱外国投资、政治上转向正式的多党民主制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这些举措却遭遇到了赞比亚的“资源民族主义(resource nationalism)”这种新兴对立政治(new oppositional politics)的抵抗。这种政治和在非洲和在拉丁美洲发生民族主义状况一样,都是要求本国人民在本国和外国持有的天然财富中要占据更大的份额,并且对劳动剥削、社会发展不足以及腐败政府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家资源等现象表示十分的不满。资深赞比亚政治家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卢萨卡州长(governor of Lusaka),90年代担任齐卢巴政府部长,21世纪初创建了自己的政党“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这时以“赞比亚人支持穷人”为口号,以资源民族主义为政纲,抨击齐卢巴政府出卖本国利益给外国投资者,并指责中国从开普敦到开罗一直实行奴隶制。这时,中国国有企业就被视作一个特别的目标,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外国主权国家,而不仅仅是私人投资方。
但萨塔在2011年大选获胜后缓和了言辞,并表现出一连串姿态来安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与查韦斯(Chvez)、莫拉莱斯(Morales)或科雷亚(Correa)等拉美国家领导人相比,萨塔在任期间谨慎行事,仅仅将矿产使用费从3%提高到6%(根据销售收入计算,而非利润),并将最低工资从 35万克朗(合70美元)提高到50万克朗(合100美元)。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人们对社会变革和经济改善的期望,同时提升了萨塔作为誓死与外国投资者斗争的赞比亚领导人的形象。2013年11 月,当矿业巨头Konkola铜矿公司(KCM)宣布要解雇 1500 名工人时,萨塔立即吊销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作许可,并威胁要吊销整个公司的采矿许可证。萨塔政府还启动了全行业的法医审计,以征收这些公司的全部税款。
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态势重新界定了21世纪外国资本进入赞比亚的政治经济条件。此外,多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捐助者实施的强制性结构调整方案,1990年代矿业私有化推进了赞比亚铜矿带资源的国际化。当我于2008年抵达赞比亚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地已有不止有2家,而是有10家大型外国矿业公司。它们不仅来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还来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包括印度、巴西和中国等国家。这无疑让赞比亚政府拥有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全球资本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赞比亚的发展,但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化约为社会学经典的“核心-边陲”格局。在赞比亚取得独立50年后的今天,尽管这个非洲国家在发展能力方面存在种种弱点,但它并不是符合那些刻板印象中“遭受掠夺”或“失败”的非洲国家形态。爱国阵线政党(萨塔所创建的)的崛起表明了这一点。虽然竞争性选举可能并不能带来良好的政府,但它们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向现任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并要求其面对外部投资者表示出更多的民族自信——并且能够表现出这样一种可能性——非洲政府确实有能力为了实现本国民众的利益,而对外国资本做出抗拒。